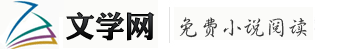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:小说主人公是阮郁珠秦帜的名称叫《阮郁珠秦帜》,这本书是作者阮郁珠倾心创作的一本古代言情风格的小说,小说中内容说的是:人不是他一样。偌大的宫殿,她遣走了所有人,生怕走漏了一点风声,眼前之人便万劫不复。阮郁珠压抑着,很...

昭国皇宫,沉沉大雪压着重重黛瓦。
大殿里,帝阶上,女帝阮郁珠面无表情的俯视着站立的国师秦帜。
秦帜姿态恭敬,面色如常,好像要和信王一起图谋造反的人不是他一样。
偌大的宫殿,她遣走了所有人,生怕走漏了一点风声,眼前之人便万劫不复。
阮郁珠压抑着,很平静地开口:“国师昨日去了何处?”
秦帜拱手,恭敬而生疏:“臣记得陛下少年时喜欢宫外的糖人,昨日本想给陛下带些回来,只是……那小贩却不见了。”
听着他的话,阮郁珠的眼神一点点暗下,如黑夜将灭的灯烛。
她喜欢的从来都不是糖人,而是因为他送的那对糖人牵着手,像极了那时的他们。
而他昨日又哪里是去买什么糖人,案上的奏折本本都是在弹劾他面见信王谋臣!
眼前人是心上人,却未必再是少年人。
阮郁珠心尖微颤,却是淡淡一笑:“国师从前在无人之时都是唤孤珠儿,孤仿佛已经许久没有听到过了。”
秦帜眼神一沉,语气如这寒冬的雪:“臣惶恐,怪臣年少时不懂事,冒犯陛下,如今自当恪守臣规。”
阮郁珠自嘲一笑,或许亦是无奈。
年少时不懂事,那年少时的情意莫非也是不懂事吗?
那她又是为何如此执着?
阮郁珠闭了闭眼,只问他:“你还记得,我大昭的国师,最要守的是什么规矩吗?”
秦帜眼神一凛,第一次抬起头来望向那帝阶上高高在上的女帝。
他神情恭肃,却似话里有话:“昭国国师,历来只守护女帝一人,臣,亦是如此。”
阮郁珠心中一痛,看来,他不是忘了他的职责,只是想守护的人不是她了而已。
国师只需守护女帝,女帝却可以不是她阮郁珠。
阮郁珠看着他,如此陌生又熟悉。
以秦帜之心智,他如何会不知道,若是信王篡位,那她便只有死路一条。
他甚至都不在意她的死活了吗?
容颜未逝,君心已改,年少情谊,终究开败。
阮郁珠的眼神沉了下去,心口似有利刃刺入:“国师记得便好,退下吧。”
秦帜又看了她一眼,无声退出了大殿。
阮郁珠定定看着他的背影,有那么一刻想要追上去,可脚下却没有挪动半分。
脚下这九十九级帝阶,是他们永远迈不过的距离。
她转身看着案上的奏折,深深吐出一口浊气:“裴瑜,将这些折子烧掉,呈上这些折子的大人,每人赐酒一杯。”
亲卫裴瑜愣了一下,才垂首:“遵命。”
第二日早朝。
阮郁珠下令放干国运河。
满朝文武跪了一地,帝师齐老太傅气得一双枯瘦的手都在发颤。
他巍颤颤拄着拐杖,指着她大喝:“国运河乃我昭国命脉之河,陛下如此,上对不起昭国历代圣君先帝,下对不起万民百姓,必失天下人心!臣不能看陛下如此!”
阮郁珠抿唇,咬牙道:“此事师父不必再劝,孤,非做不可!”
她狠下心来:“来人,将太傅扶下去!”
两个侍卫阔步上前,扶住齐老太傅。
可齐老太傅一把推开侍卫,将手中的拐杖狠狠扔在地上,老泪纵横:“既拦不住陛下,臣愿死谏!”
话音刚落,他便向大殿的玉柱上撞去!
宫门重重,锁住了皇城的冬。
阮郁珠一步步,漫无目的地走过一扇扇宫门,背影萧瑟。
裴瑜上前禀报:“陛下,老太傅没事,只是受了点皮外伤,养养就好了。”
阮郁珠心中压抑着的一口气,这才松缓了一些。
这时,前方的宫门缓缓而开,阮郁珠抬头,便看见秦帜黑沉着脸从里面走出来。
原来不知不觉,她又走到了秦帜的无极宫。
见到他脸上愠怒的神情,阮郁珠微微垂了眸:“你们先下去吧,孤与国师有话要说。”
所有人退到远处,整条宫道只剩下他们二人。
秦帜语气冷意四溢:“中书侍郎等人为了大昭夙兴夜寐,忠心耿耿,陛下究竟为何要赐下毒酒?”
阮郁珠静静看着他,没有说话。
正是因为他们太过忠直,所以只要他们在朝堂一日,他与信王勾结的事情就瞒不住。
到时候,谋逆大罪压下来,即便她是帝王,又能护他到何时?
她不杀他们,死的便是秦帜。
秦帜见她不语,脸色更是难看:“陛下如此屠戮忠良,难道就不怕寒了天下人心吗?”
月光下,他眼里的愤怒如一捧休眠的火山,几乎要喷薄而出。
阮郁珠攥紧了手,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,沉沉的,堵得慌。
他挂记天下,怎么偏偏就忘了,这天下如何,与他这国师有何相关?
大昭国师,自始至终只有守护女帝这一个职责。
阮郁珠心酸不已,忽然苦笑一声。
她看着秦帜的眼,轻轻说:“国师,你也不要寒了朕的心才是。”
说完这句话,她不想再看他现下表情,转身往回走。
清冷的月光下,她的背影渐远,像是逆着众生而行的一道孤影。
雪又零散下过几场,长乐宫里,阮郁珠正批着奏折。
裴瑜匆匆从殿外而来,跪在禀告:“陛下,信王的兵马已经到了兖州,一路秘密潜行,不出五日便要到皇城了。”
殿中的火盆跳响一声,阮郁珠手中笔尖掉下一滴墨点,纸上顿时便氤氲了一团墨黑。
她的心,跟着颤了一下。
终于,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
阮郁珠沉吟了片刻:“让兵部严大人前来议事。”
严大人奉诏急急前来,带了一身寒气:“陛下,前几日京城周遭来了一伙悍匪,西都兵马被刑将军调走剿匪了,前阵子兖州水灾,东都兵马又被国师调去救灾了。”
阮郁珠眼神一暗,心头窜进一股寒意。
西都的刑将军跟秦帜交好,此时离开,意思不言而喻。
看来,他是真的要跟信王里应外合,死了心的要夺她的云山了。
阮郁珠的心里裂开了一条缝,迎着这凄然大雪往外渗血。
严大人退下后,阮郁珠背手站在窗边,天边寒月渐圆,今日又到了十五月圆。
她突然问:“九十九个死囚,准备好了吗?”
裴瑜应道:“准备妥当。”
阮郁珠看着天边,心便如同这漆黑夜幕,找不到出路,寻不到归途。
最终,她只是沉重一叹,语气更是无奈:“跟从前一样,善待他们的家人。你去请国师来未央宫饮宴吧。”
翌日,天色微晓。
阮郁珠推开大殿沉重大门,寒风轻拂,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猛冲而出。
身后,殿中尸体不断被抬出来。
见此场景,刚刚从侧殿醒来的秦帜脸色阴沉至极。
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命啊!
他攥紧拳头,太阳穴青筋毕露,语气像是从牙缝中挤出:“这些都是大昭子民,陛下如此嗜杀与暴君有何区别!”
阮郁珠眼神复杂的看着他,没有正面回答,反而问道:“是否在国师心中,孤就是这样一个残暴昏庸的君王?”
秦帜脸色一变,却更逼近一步:“臣不敢,只是陛下如此滥杀无辜,大兴土木,甚至于伤了老太傅的心,难道不怕最后众叛亲离吗?”
众叛亲离……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吗?
阮郁珠身影一僵,苦味在口中蔓延直至心脏。
滥杀无辜也好,屠戮忠臣也罢,无论哪一条罪都是让世人唾骂之大罪。
她担不起,却每一条都只能默默背负。
她深吸了一口气,硬下心肠,冷声道:“孤是君王,你是国师,莫忘了你的职责,便是全天下与孤为敌,你都是要站在孤这边的!”
这是昭国帝王与国师的宿命,也是他们注定的宿命。
秦帜顿在了原地,他如冰的的目光一寸寸巡视过阮郁珠的面庞,终于,他松开紧攥的拳头,又恢复了淡然的国师模样。
他说:“臣,不敢忘。”
雪缓缓落在他肩头,眼前人眼里却没有她的影子。
明明一步之遥,却似有千山之远。
阮郁珠看着他,心口骤疼。
她无力的转过身,挥了挥手让他退下。
国与万民都沉沉压在她肩头,可偏偏,她手中还捧着一份不可触及的情爱。
秦帜踏着雪往无极宫走,忽然停了脚步。
他转头看着殿前屹立风中的阮郁珠,又看着那殿前蜿蜒了一地的鲜血。
他回过头,冷冷吩咐身后侍从:“通知信王,可以动手了。”
……
过了两日了,无极宫书房里。
秦帜手里拿着书,视线却不知道落在了哪里。
侍从进门来报:“国师,陛下今日突发奇想,要去皇陵祭拜先祖,随行只带了九十九亲兵护驾!信王殿下已经带兵去了……”
秦帜合上手中书,脸色一变:“走,去皇陵!”
马匹疾驰,耳边长风簌簌而过,秦帜靠近皇陵,便见信王兵马。
他勒马上前,只见信王明浅一身兵甲,身上还沾着血迹,显然方才与人交过手。
“陛下在何处?”秦帜急问。
明浅得意大笑,挥手让人抬了一具盖着白布的尸首上前。
秦帜看着白布,浑身一震,几乎摔下马去。
她……死了?
“听说她只带了九十九亲兵来皇陵,本王带了三千劲旅突袭,她在奔逃路上马车坠崖,本王捞回了她的尸首!”说完,明浅掀开了那块白布。
眼前的尸首面目全非,但穿着女帝的衣服,腰间更有先帝亲传的鸾凤玉佩。
秦帜脚步沉重地走上前,看了一眼,眉头微蹙:“不是她。”
空气忽然一时凝滞。
紧接着,四面忽然响起脚步声。
信王明浅看着四面而来的兵士,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居然被包围了。
人群中让出一条道来,阮郁珠一身便服走出来。
她的目光直直落在秦帜身上,眼神复杂难言:“国师,到朕身边来。”
秦帜站在原地,两人四目相对之间,他忽然明白,这一切不过都是她的设计。
他的眼神跟着沉了下去,果然是帝王心术,从头到尾,她明明什么都知道,却将他摆弄于股掌之中。
是了,她是帝王。
阮郁珠见秦帜站在原地,最终没有选择走到自己身边。
她的心缓缓黯淡下去,冷声道:“信王意图谋反,难道国师今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,护着她吗?”
却见秦帜挡在信王跟前,字字辩护:“陛下误会了,信王是听臣传信,怕陛下有危险,特来护驾的。”
一旁的明浅也连连称是:“是啊,陛下,臣是特来护驾的。”
阮郁珠站在原地,暗暗攥紧了五指,眼眶发红。
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性命在逼她,若此刻她说信王是造反,那他秦帜就是主谋。
如今三军在前,这谋逆大罪下来,天下共诛,难道要她杀尽三军来护他一命吗?
曾经发誓要护她一生的人,如今,却用自己的命威胁她,去护另一个要杀她的人。
阮郁珠忽然拔出剑,寒光闪过,剑锋落在了秦帜脖子上。
她红着眼:“你当真以为孤不舍得杀你吗?”
秦帜看着剑身倒映出她头上帝王玉冠,表情僵硬:“臣从未如此以为。自古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,陛下动手便是。”
他闭上了眼。
阮郁珠死死握着剑,手不易察觉地在颤抖。
他是死了心要护着明浅的了,哪怕与她为敌。
阮郁珠的心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低泣,她的声音压抑着难以言喻的沉重:“孤知道,今日孤不杀你,来日便是孤死在你手中。”
可是,那又如何?她情愿死在他手中,亦不愿伤他分毫。
“哐当——”长剑落地,她拂袖而走,却更像是个战败的逃兵。
长风冷冽,吹起秦帜的衣袍,雪花掉在他眼睫上,一片冰凉。
阮郁珠的背影在他眼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,直至消弭成无数人群中的一点。
皇城。
无数宫门幢幢,绵延着清冷。
阮郁珠案前是日复一日批不完的奏折,书房的烛火微微摇曳,映衬着她的脸忽明忽暗。
放下手中的折子,她有些疲累地揉了揉眉心。
裴瑜从殿外上前回话:“陛下,信王已经被软禁起来了,可是国师……要如何处置?”
阮郁珠的身子僵了一下,有些颓然地靠在大殿的座椅上,眼前是空荡寂静的庄严大殿。
处置?她能如何处置他呢?
最终,她只是轻叹一声,挥手:“放了吧,孤,又能拿他如何呢?”
对他,她从来无计可施。
终究,他不过是仗着她的爱,所以才这般肆无忌惮。
裴瑜领命,刚要转身,却又忽然顿住了脚步,躬身道:“陛下,国运河已经挖得差不多了,最迟还有三个月,祭坛就能出来了。”
三个月……
阮郁珠心里默默念着,抬眼看向殿外夜色,声音低沉:“要快,孤,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”
这夜的风雪很大。
阮郁珠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寒风呼啸,辗转难眠。
她忽然想起来,少年时,每逢这样大风大雪的天气,秦帜便会整夜守在她大殿外。
他会对她说:“好好睡,有我在,不怕。”
可是如今,少年非昨日,人心已变,徒叹奈何。
看那些得不到的空,做的却是拥有过的梦。
阮郁珠缓缓起身:“裴瑜。”
她叫了两声,没有人应她。
她披了件披风,推门却看见门外大雪中,秦帜撑着油伞,立在她殿前。
这一瞬间,阮郁珠仿若回到了从前,心中竟闪过一丝心酸。
她眼中的惊喜一闪而过,一瞬又恢复如常:“国师怎么来了?”
秦帜转过身,看向她的眼神十分复杂。
他顿了顿,忽然开口:“陛下今日,杀了臣才是正道。”
阮郁珠一愣,许是殿外的风太冷,吹得她心中一阵发凉。
她何尝不明白,斩草除根,杀了他才是正道。
可是世间谁能够狠下心去,亲手杀掉自己所爱之人呢?
阮郁珠拢了拢身上的披风,一步步走到秦帜跟前:“孤还记得,未登基之前国师曾说想娶我为妻,日日同我在一起?”
“儿时玩笑,冒犯陛下。”秦帜眼神一暗,却是问她,“陛下可当真了?”
阮郁珠心中一阵揪痛。
她自然当了真,可那时候,他说的就是假吗?
阮郁珠忽然觉得眼睛一酸,深深吸了一口凉气:“天色已晚,国师请回去歇下吧。”
她不敢再多看他一眼,转身又进了大殿。
殿门沉沉关上,她靠着殿门,身体无力地往下滑。
秦帜看着殿门,又转身看着漫天铺地的白雪,沉默未语。
……
天色未曦,晨钟敲响,百官来朝。
大殿庄严,百官朝服礼毕,阮郁珠高坐君位。
礼部尚书上表请奏:“陛下勤政三载,夙兴夜寐,只是为昭国长久计,请陛下择夫,为皇室绵延后嗣!”
话音刚落,便有朝臣立时附议:“虽说自古以来国师与陛下没有通婚先例,但陛下心仪国师,臣等以为,为昭国计,未尝不可。”
整个朝堂之上,百官附议,只有秦帜站在原地,从始至终,一言未发。
秦帜看着阮郁珠,眼神却是不堪言喻的复杂,暗暗攥紧了手中的玉圭。
阮郁珠也望着他,眼中更多的却是痛苦。
如此相望不相亲,相知不相爱。
她心悦他,天下皆知。
可他呢?
回想起往日那些言笑晏晏的画面,她骤然红了眼,只感觉心脏被人两端拉扯着,生怕下一刻就忍不住掉下泪来。
“孤,今日身体不适,此事容后再议。”她的语气还算沉稳,不至于暴露心中那点怯弱。
秦帜本该拒绝,却不知为何,推拒的话一时说不出口。
但听见阮郁珠此言,便僵直地站在原地,手中的玉圭被他捏得生生碎了一角,碎玉划破手心,鲜血渗了出来。
长乐宫一片狼藉,阮郁珠将宫中的东西砸了个遍,直到宣泄到没有力气,她无力地靠坐在椅子上,眼神变得木然。
想到母君临走时,切切对她叮嘱:“珠儿,自古国师决不能和女帝成婚,不然昭国会有灭顶之灾,你是帝王,要以天下为重。”
天下为重,她为轻。
可即便她想要不顾这天下,也不能不顾他的心意。
她仰头,戚然闭上眼,将要掉下的眼泪又流回心间。
夜深天寒。
长乐宫中酒气弥漫,阮郁珠一杯接着一杯,已经喝得两颊砣红。
自从登上这帝位之后,她再也没有这般放纵过自己了,可今夜,她只想一醉方休。
兴许醉了,就能短暂地忘记那些烦忧。
殿外突然一阵骚乱,有人高喊:“来人啊,长乐宫偏殿走水了!”
阮郁珠又倒了一杯酒,却是笑了,半分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裴瑜匆匆推开殿门跪下:“陛下,长乐宫起火,请陛下移驾!”
阮郁珠饮下一杯酒,醉道:“移去哪里?他不就是想要孤死吗?孤就如他所愿又如何?”
长乐宫乃天子居所,怎么可能会有人敢疏忽至此?这皇宫除了他秦帜,还有谁敢派人在长乐宫纵火。
她若是死了,他便也能得偿所愿的让信王登基为帝了。
裴瑜拱手上前:“陛下醉了。”
阮郁珠恹恹摇头,声音略带些委屈:“孤没醉,孤只是高看了人心。”
她以为世上真情难求,郎心不移。
她以为许下的誓言就不会悔改。
可原来,到底是她执迷不悟罢了!
眼见火势愈大,裴瑜只好强行带走了已经喝醉的阮郁珠。
正阳宫。
一夜梦沉,大醉忽醒。
裴瑜跪在阮郁珠跟前请罪。
阮郁珠坐在案前,眼神带着些宿醉的迷离:“昨日是你救驾有功,孤不怪你。”
裴瑜却还是跪着未动:“昨日长乐宫大火,有人趁机救走了软禁起来的信王。臣有罪!”
阮郁珠的神色顿了顿,忽然自嘲一笑:“好一招声东击西,他也不怕真的烧死朕!”
裴瑜表情悲愤,终于忍不住劝道:“陛下,到了如今地步,切不可再手下留情了,国师在宫中已经是树大根深,若是再……”
没待他说完,阮郁珠一眼看了过去:“你在孤身边这么多年,该明白孤。”
她可以负了天下,唯独舍不得负了他。
都说君王薄幸,可能,她终究做不了一个明君吧。
“你去,请国师来。”阮郁珠看了一眼镜中人,“来人,给孤上妆。”
书房。
秦帜进来的时候,阮郁珠正斜卧在贵妃榻上。
冷冽的空气中仍能嗅出一丝酒意,他的眉头不着痕迹的一皱。
见到他,阮郁珠神色如常,叫他上前:“国师的丹青是宫中画得最好的,今日你为孤画一幅。”
秦帜淡淡一声应下,走到书桌前,执笔勾勒。
不多时,一幅传神丹青便画好了。
阮郁珠看着那幅丹青,嘴角微微上扬:“还是只有你才能画出孤的神韵,只可惜,国师跟孤终究不是一条心。”
说完,她脸上的笑意便淡了下来,一手将那幅刚画好的丹青丢进了火炉里!
火苗一下吞噬了阮郁珠画中的眉眼,秦帜脸色一沉。
阮郁珠定定看着他,难掩眼中悲寂:“秦帜,是不是孤不做这个女帝,你便能站在孤这边?”
秦帜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,眼里却幽深一片。
他拱手道:“陛下醉了。”
陛下醉了,他却很清醒。
关键字: